
本名之櫆,字白华、伯华,籍贯江苏常熟虞山镇,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小南门。中国哲学家、美学大师、诗人,南大哲学系代表人物。

受访者:王鲁湘
著名文化学者 ,1956年生于湖南,1978年进湘潭大学中文系,1982年毕业留校, 1984年进北京大学研修中国美术史,并获哲学硕士学位。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,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,李可染画院理事长,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 ,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。历任凤凰卫视《纵横中国》总策划、《世纪大讲堂》主持人、《文化大观园》总策划、主持人,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导,北京凤凰岭书院院长。
作者:周建朋
清华大学美术学院,博士
北京大学艺术学院,博士后
2007年任教于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
现为大理大学滇西民族艺术研究院院长、教授、硕士生导师
“宗先生告诉我,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出土文物上,一定不要从书本到书本,做一个书斋学者。要勤去博物馆、美术馆,多看实物。不要说起美学理论一大堆,看起实物来,既不辨真假,也不识高低。宗先生的病榻教诲,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影响甚巨。”
——王鲁湘
1986年的今天是宗白华先生辞世的日子。王鲁湘先生回顾宗先生去世时的经历,我听后很无奈,良多感慨。特殊的年代,历史的记忆,也是文人的无奈!
我问鲁湘先生:“在细雨下,点碎落花声!在微风里,飘来流水音!宗白华先生走得是否这样轻盈而有诗意”?
“1986年,我在北大哲学系攻读中国美学史专业硕士学位,导师是叶朗先生。宗白华先生年事已高,不再教课,系里也让学生包括进修教师尽量不要去打扰。记得是刚进11月,冷得很早,但还没有供暖,系里工作人员找到我,说宗先生昨晚摔了,赶紧过去看看。我就去了朗润园先生的家。家里就宗先生和宗师母两人,宗先生89岁,宗师母好像还大两岁,腿脚倒还利索,但全聋。原来是晚上如厕摔了,倒不严重,只是一个情况让我揪心:宗先生有前列腺肥大,尿频,但又撒不出,所以老要如厕,家里只有比他年长且全聋的老太太,摔出多大动静都无人知晓。我就叫了校医院的车将宗先生拉到了北大校医院。
那年代的北大校医院就在勺园东边,一排灰色二层楼,很简陋。接诊大夫了解情况后同我说这里没办法,要转院。我问转哪?说北医三院,说那里有一个伞状的导尿管,插进尿道后不会轻易掉出来。于是我就陪宗先生坐北大校医院的车去往北医三院。
北医三院是北大教师的定点医院,在北大的东边不远。人很多,照例挂了号后坐在走廊的木板凳上等喊号。西北风呼呼地灌进来,很冷。宗先生一会儿就要起身去厕所,我搀扶着他一步一挪。到了厕所,帮老人家解下裤子,站一分钟,滴尿不出,又示意我系上裤子,再一步一挪回到过道。刚坐下,又起身,尿急,又一步一挪去往厕所……如是者不知多少遍,就是滴尿不出,老先生痛苦不已,又愧疚不已,我也累得不行,又急得不行。

(宗白华)
宗白华先生总也等不到叫号,又眼见好几个人插队,显然是有关系者。我进到诊室,向大夫说明外面这位老人九十岁了,是北大著名教授,已经快被尿憋死了,能不能先看?大夫头都不抬,说等着吧!我说刚才明明有人后来先看了,照顾一下老教授不行吗?大夫声音仍然冷若冰霜:不行!大家都等着。我一下怒从胆生:“等你妈个x!”一把就把桌子掀了。那年我三十,火气旺,脾气大。这一下惊动了,来了好多穿白大褂的。我把宗先生从过道扶进诊室,放到小床上,愤怒地大喊:“你们还有人性吗?”
有一个中年女大夫,可能是领导,一边安抚我,一边让那大夫赶紧看看。这时我气也消下来了,就把情况介绍了一下,特别提到伞状导尿管。他们几个医生都说没有听说过有这东西。我说能不能留院观察治疗?他们说没有病床。建议先回北大校医院。这时天也快黑了,只好又把宗先生扶上那辆破车回校。说破车一点儿也不为过,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后面两扇门关不上,是用铁丝缠着门把。
回到校医院,医生不想收院,还是让送回家。我一听这怎么行?且不说老先生已快被尿憋死了,回到家只有一个全聋的老太太,再摔倒扶都没人扶。我坚持把宗先生先放医院,赶紧去找我导师叶朗先生。叶先生又领着我找到系主任朱德群家,我们又一起找到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家,听着书记给校医院领导打电话,无论如何今晚必须把宗先生留院观察。我赶紧又赶回校医院。
校医院确实也没辙,像样的病房一时也腾不出来。我记得那晚,宗先生住的房子里面堆满了医用氧气罐。第二天一早,校、系领导都来了,美学教研室的老师也来了。阎国忠先生的夫人在北医三院工作,于是托她去走走关系,看能不能安排张病床。下午答复来了:有病床,还锁着三间呢!但宗先生不够格呀!我们一下懵了:什么格?连宗先生都不够格,谁够格!
只有这时候,一个残酷的现实揭露在我们面前:原来,北京的大医院都有特殊病房和相应的治疗体系,比如说一级教授可以住进友谊医院高干病房,如朱光潜先生,上半年去世,就住友谊医院。宗白华先生是三级教授,50年代评的。新中国成立后,所有大学哲学系取消,原有教员统统集中到北大哲学系,职称重新评定。宗白华是原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,因为这个政治原因,评为教授中最低级的三级,而且此后终身不曾给学生开课,仅在60年代初给进修教师上过三堂课。
皮球踢回来,要住院先解决级别问题。这时校长办公室通知我去一趟校统战部取一封信,是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给友谊医院的。原来北大统战部得知宗先生的事情后,给卫生部部长写了一封信,把宗先生的情况说明了一下。因为历史原因,宗先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,他完全可以享受一级教授的种种待遇,建议安排进友谊医院高干病房。崔部长马上批了。我带上这封信,还是坐那辆校医院的破车,把宗先生送到了友谊医院。
没想到办住院手续时,院方说只能住15天,15天后来把人接走。我想反正已经住进来了,管他呢!15天后,果然通知接人。无奈,又是那辆破车,在北京的凛冽寒风中接回了宗先生,住进了校医院。虽然通过导管导尿,减轻了宗先生的痛苦,但连续的拔插也引发了尿道感染,加上路上受了风寒又并发肺炎,宗先生回校不久就去世了,距他九十岁生日还有一个月。
在病榻前,宗先生告诉我,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出土文物上,一定不要从书本到书本,做一个书斋学者。要勤去博物馆、美术馆,多看实物。不要说起美学理论一大堆,看起实物来,既不辨真假,也不识高低。宗先生的病榻教诲,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影响甚巨。”
鲁湘先生在叙述完后,加了一句:“谢谢各位!三十二年积郁,终于一吐为快!”
听完鲁湘先生的叙说,不知有何感触?我想起了宗先生的几句诗:
“世界的花,
我怎能采撷你?
世界的花,
我又忍不住要采得你!
想想我怎能舍得你,
我不如一片灵魂化作你!”
庞贝遗址出土的一幅壁画《采花的少女》,暖黄色调,一位弯腰采花的白衣少女,一篮子野花,那宜人的美是如此清新而迷人。于是又想起宗先生的话来:“当你散步的时候捡起路边的燕石,折下路边的野花,置于案上,不必珍视,也不必丢弃,权当散步的纪念吧。”

(《采花的少女》)
人生的美是在平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和见到的,也是平常生活本身,鲁湘先生与宗先生的经历也是美本身,他陪伴宗先生走过了 人生的最后岁月,有些人情的冷漠和世事的无情,还有无奈,然而还是伴着美的,虽然这份美的背后还有些心酸。
人总是要走到尽头的,每个人都不例外,有的人活着但好像和死了没有区别,而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,而且永远活着,比如牛顿、比如宗白华先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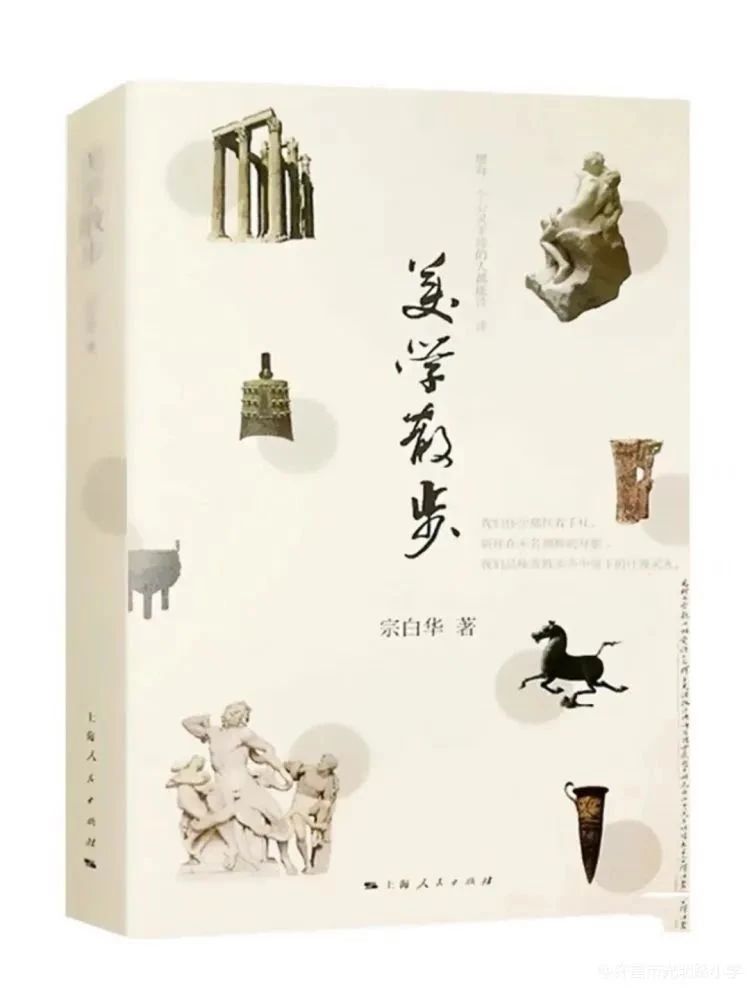
(宗白华《美学散步》)
禅带给中国文人的首先是智慧,还带给我们对死的理解和意义,所以成为文人最喜欢的一种智慧和方式,阿弥陀佛的境界也是智慧者的境界,愿先生已在那铺满莲花的只有美的世界。
(作者单位:大理大学滇西民族艺术研究院)